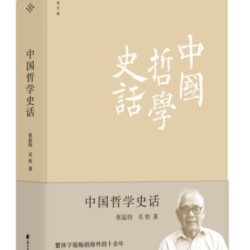Эпизоды
-
孟子揭示王道真谛:无需高深莫测,只需换位思考,推己及人,便可实现仁政。他巧妙运用"善推"原则,让敬老爱幼、人性弱点皆成为施行王道的桥梁。孟子智慧非凡,将崇高难行的王道仁政化为切实可行的道路,赢得君王与民众的广泛尊重与推崇,从而有力地推动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。
02:04 孟子的聪明才智:儒学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
他不仅循循善诱,而且能提供简单易行的途径,使那些昧义逐利、脑满肠肥的君王们感觉到“从之也轻”。孟子告诉他们王道仁政并不是高不可及的事情,只要把自己的心情反省一下,想想自己如此,别人也如此;而能推己及人,见诸行事,那就是王道的精神了。古来的圣王所以能行仁政而王天下, 并没有什么诀窍,其关键就在善推所为以及于百姓而已。所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,天下可运于掌……故推恩足以保四海,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,善推其所为而已矣”。
在这“善推”原则的活用下,不仅敬老怀幼是德政,就是许多小疵又何害于王道的推行?例如齐宣王坦白地承认他好货好色,孟子却告诉他没关系,只要能同时想到别人也一样的好货好色,而能替别人解决问题,那就是王道了。
王道仁政本是崇高伟业,难以着手,但在孟子手中竟是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,无往而不能行了。试看他是多么的聪明而有办法?岂是那些徒 诵 章句、食古不化的俗儒所能比?正因如此,他才能博得君王的崇敬、社会的景仰,而有效地弘扬孔道。他当时是: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,传食于诸侯。”
孟子声势之大,中外古今还没有第二人。这并不是什么排场和气派,而是说明孟子在朝野间具有何等的影响力。以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弘扬孔道,那就无怪乎孔道大行了。
-
孟子一生的抱负就是要继承孔子、弘扬儒道,这一使命孟子是有声有色地完成了。孔门弟子虽号称三千,贤者达七十;然而大抵只是些颂经乐道的君子。他们对谨守师说、努力做人,尚能各有所长;至于发扬孔子之学,光大孔子之业,却无此才气。纵使颜渊不死,也不过对孔子的学术思想能有极高的领悟而已;若想有魄力有办法地弘学救世,使人接受孔子之道,那也绝非他之所长。因此假如没有孟子出来,则孔子的精神势必为其平淡的外貌所掩埋;孔子的大道势必为那些浅见的众人所摒弃,还哪里会其道大行,尊为至圣?孟子所以能达成这一辉煌使命,一方面在其能阐扬孔学的精义,使学者能认识孔学的伟大价值;一方面在其能有办法慑服那些拥有威权的君王政要,使他们尊崇孔子的地位。唯有这些代表社会权威的人物能崇敬,然后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信奉。
博取学者的服膺很简单,只要你拿出真东西来,他自会识别而信从;但是要说服君王权贵则不简单了。他们不学无术却居高位而拥大权,哪里听得进你那书呆子的理论?但是孟子有掀天撼地的气魄,摧慑其声威;有操纵自如的本事,导使其就范。君主们的崇高地位,孟子根本没放在眼里,他说:
“说大人则藐之,勿视其巍巍然。堂高数仞,榱题数尺, 我得志弗为也……”
他们的骄矜自满,孟子只消两句话便给封回,使其驯服地听他教训。例如齐宣王初见面时,第一句话便得意地问孟子:
“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?”希望能从孟子的回答中,表现表现自己的神气。哪知睿智练达的孟子却一百个不屑一道的样子,硬说不晓得,要谈就谈王道罢!谈王道当然便是孟子的一套了。(按:孟子如据实而对,下面的话便只有恭维齐国和齐王了,那还谈什么?难道孟子是来听训的么?)有时君王们对某些行为感觉惭愧不安,孟子不但不加责难,反而指示彻底贯彻的办法。怎样才能彻底贯彻呢?那就又是王道的一套了。尤其他对齐宣王讲“好乐”那一段,简直就像师长父母哄着小孩用功上进一样。我们说孔子循循善诱,但孔子所诱的只是学生,孟子却是对君王权贵循循善诱了。
-
Пропущенные эпизоды?
-
这善良之性虽微弱不显,但一经存养发挥,便将如“火之始然,泉之始达”,而有辉煌灿烂的表现。这时我们恻隐好善的本性不仅灵明显著地存在于胸中,而且充沛诚挚地形诸于外境。它势必一方面由己身而扩展到他人和群体,一方面由主观的意念而见诸于实际的效益。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仁心善性不仅程度增深,范围扩大,并且要具体地加被于社会人群,使社会人群真能受到我们的泽惠。唯有如此,我们这仁心善意才算真正地美满完成。我们所以要设官分职、作君作师,所以要分田制产、为民谋福,就是要把我们的仁德善意客观化,以便其有组织、有力量地实现和完成。而一个仁人志士所以献身政治,推行仁政,也就是出于这股仁心的推动。因为他们强烈的仁心善意使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危、人民的祸福,感到是自己分内的责任。所谓“思天下之民,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,若己推而内之沟中”,因此便势必要挺身而起,为人群服务了。
但是要把这仁心善意完美地实现出来,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因为世间的事并非照着我们的意志而安排,许多事与我们的意念不能配合,因而构成推行的阻力;同时又有许多事,深合躯体的欲念,诱使我们乐此不疲,以致忘掉,或违反了我们为仁好善的本意,这时必须有坚定的道德勇气,才能克服一切,贯彻初衷。以上还是就个人而论,至于施政为邦,事态复杂,必定要碰到许多便利可欲却伤仁害善的事情,以及许多诱惑多端、似是而非的事情。这时就更需要能通观体要,明辨权利,而选择我们应走的途径。一个真有修养的人绝不会被任何物欲诱惑而动摇道义的信念,绝不会在任何威胁困难下,放弃为仁行善的原则。所谓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 能屈。”只有达到这种程度,才真能“铁肩担道义”,才真能堂堂地做个大丈夫。
-
当孩童落井,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?这种纯洁的同情,是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本性?如果人人生来善良,为何恶行频发?原来,善与恶的萌芽同在一个基础上,它如何发展,取决于我们的选择。
02:01 人性的双重性:努力的方向与挑战
这段话的关键在于“乍见”和“将入”。“乍见”是说没有任何心理的准备。“将入”是说事态正在进行的过程中。合起来也就是说:任何人在心理上空灵无住的时候,突然看见孺子落入井中,便必定会发生一股纯洁的“怵惕恻隐之心”。只这一念的恻隐,就足以证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。从这里面绝不会发展出丑恶的败德;相反的,它正是仁的源泉,它就是一切美德的种子。只要让它合理地发展出来,就自然形成人们的道德仁义。否则人们的高风美德将成为无源之水,纵加以塑造,恐怕也难实现了吧!
或者说:既然人性本都善良,何以未见人人都善,而那丑恶之事却层出不穷呢?原来人们恻隐好善之心虽也如饥食渴饮一样,都是 与生俱来的本性;但它并不如后者那样具体显明。饥食渴饮可凭生理的反应来告知人们,并迫使人们去追求;恻隐好善之心却奥妙精微,只能凭心官的反应才能体现。心官用思,自然反应清楚;心官不思,便势必意识模糊,而为强烈的躯体欲念所淹没。一旦欲念越出常轨,便随之而为恶了。其实推本溯源,他的本性仍是善良的。这就如牛山之木一样,牛山本是佳木葱茏的,但因地在齐国近郊,树木便为人砍光了。我们既不能因此便说牛山不生树木;同样的也不能因为有人为恶,便说人性不善。
从上面看来,人既有善良的本性,也有善性泯灭,纵欲为恶的可能,他实具有可好可坏的双重性。而在这可好可坏之间,便产生了人们努力的课题。人们如果心官失明无主,专从躯体发展,纵不为恶,也是禽兽世界。因为他只表现了和禽兽共有的性能,而未显露出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”的地方。反之我们心官若能灵明有主,把这善良本性保持而加以发挥, 那才真是表现了人与禽兽不同的特征,而真正做到了“人”的要求。
-
然而批评各派思想,只是孟子弘扬儒学的消极一面。光靠这一面的努力并不够用;更重要的是他能积极生动地发挥孔子的精神,使得人人都能接受。同时他又在学理上给孔子思想建立有力的哲学基础。
孔子教人“做人”,其旨趣在使人做到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而已。他虽有“仁”的中心思想,但只是以仁者的境界和做法来勉人,对于“仁”的理论并无说明;虽则在他心中是有一个深厚圆融的“一以贯之”的思想系统。其实这本来也无须说明,做人的好坏,世道的兴衰,与哲学知见毫无关系。诚如陆象山所说:“若某则不识一个字,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。”但孔子既没之后,百家并起,以学争鸣。这时一切主张教训,便必须有其理论的说明才足以折服人心,以对抗他家的辩难。否则纵有金箴zhen1宝训,也无法使人理解和接受,当然更谈不到服膺ying1奉行了。因此孟子便势必要把孔子的主张说出个原委来,以与百家之学相对抗。
首先要说明的是孔子学说的“客观性”。大家都知孔子的中心思想是“仁”。孔子千言万语勉人为仁,并不是出于孔子的私衷所好;相反的,“仁”乃是人们的本性。它是亘古以来与人俱存的,不过孔子把它明确地指出来,一如牛顿指出地心之有吸力一样。因此人们为仁,并不是劝人矫揉造作,塑造成孔子一己的蓝图;也不是孔子个人有什么特殊的目的,想借此来实现。那只是把人们潜在的本性完美地发挥出来而已。这就如花的开放、果的成熟一样,完全是顺尽自然之性。
但人性果真是本质良善,能产生“仁”的美德吗?假如人性本质是丑恶的话,那岂不是愈发挥就愈丑恶,愈给人类带来更多的问题吗?孟子很坚定地告诉我们:人性是善的,他并且举出一段精彩的例子来证明。他说: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,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,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,非恶其声而然也。”
-
又有一次,孟子在滕国遇到一位儒生陈相。这位陈相听了许行的一番宣传,便要脱离儒家,去追随许行。而这位许行, 乃是一个小集团的领袖。他的信徒有数十人,都是穿着粗布的衣服,而且自己织衣穿、织席睡。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自耕而食,没有劳心劳力之分,即使是君主,也应与人民同耕,不可依赖俸禄以自养。由这种说法,可知许行是一位兼有杨朱思想的墨者。因为他的自耕而食,像杨朱;而他的苦行精神,似墨者。如果套用现代的观念,它似乎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。
孟子认为许行的做法是极端的、荒唐的。因为天生万物, 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,每物有每物的特点,每物有每物的功用。同样,每人有每人的能力,每人有每人的欲望。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农夫、工人又是商贾,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生活,而必须有社会的生活。社会的存在,就是为了分工合作,调整彼此的需要。有的人劳心,有的人劳力,这并非在基本人权上有所差别;而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中,应该有这样的安排。所以许行提倡与民同耕的理论,无异否定了个别的差异、社会的组织。
孟子这番话,是从人性的根本上,从社会学的观点上,批评杨墨的。其间并无意气用事的地方,请看他的解释:“杨墨的学说不灭,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挥。于是邪说引诱人心,道义被遗弃,造成兽食人,人食人的危机。我担心这种危机,所以要发扬先圣的学说。”这是孟子批评杨墨,发挥儒学的抱负,岂是为了好辩逞强?所以有一次他的学生公都子问他:“别人都说你好辩,这是什么缘故呢?”孟子却问答说:“我哪里是好辩,只是不得已罢了。”为什么不得已?为的是要“正人心,息邪说”。以尽其对社会、对人类的责任。
-
探究孟子如何揭示人的社会本质!孟子批判阳末苛求离群独行,嘲讽杨朱自私至上,比拟墨家治标不治本。在讲述人性应如何发扬光大的曲折辩论中,我们能否在今喧嚣世界中找回适度与舍己?来听故事,找答案。
02:04 墨家与儒家:战争背后的不同立场与价值观
但我们要知道孟子生在杨、墨之后,但他并未和杨、墨本人发生正面的冲突,他所批评的是当时那些服膺 ying1 杨、墨思想的人物,我们在《孟子》一书中,可以找到许多和这些人物辩论的故事。
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隐士,叫作陈仲子,他洁身自好,显然是杨派的人物。孟子却骂他是一条蚯蚓,因为他无求于世, 不以物累形,正同蚯蚓一样,上吃泥土,下饮黄泉。孟子以为这种行为有点想不通,如果仲子认为人间的东西都是罪恶的话,试问仲子住的房屋是谁造的?隐士们都主张为我,当然没有隐士造房屋给仲子住了。孟子批评仲子的这段话,就等于批评杨朱的为我思想。因为“人是社会的动物”,人不能离群索居。在生存竞争上,固然必须互助合作,才能征服自然;而在人性的发扬上,尤其要通过社会的关系,而把人们潜在的德性才华发挥出来。在鲁宾逊的荒岛上,是产生不出孔子、耶稣、杜甫、歌德的。现在,如果抛弃了人与人的关系,而一味追求自我,这与动物的自来自去,又有什么差别?所以孟子要骂杨朱为禽兽,骂仲子为蚯蚓。
孟子和墨派的人物接触较多。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墨派的宋牼keng1,他正赶着去调停秦楚间的纠纷。孟子便问他用什么方法去说服秦楚的君主。他回答说:“我将告诉他们这次战争对他们不利。”孟子却毫不客气地说:“先生的热心使我钦佩,而所用的方法却不敢领教。”为什么呢?虽然孟子和宋牼同样地反对 战争,但孟子对宋牼的不满,只是因为宋牼忽略了一个大前提,宋牼不知道义利的分别。孟子以为反对战争,是由于战争抢夺土地,屠杀生灵,是不合道义,所以要反对。而墨家以利来止战,无异扬汤止沸,舍本而逐末。试问假如战争能对之有利,就打仗吗?由此可见孟子和墨派人物的立场不同,一个是树着道义的旗帜,一个却以功利为号召。
-
孟子,儒学巨擘,一生追求仁政,对抗民贼。竭力推广儒家思想,同时硬碰硬地批判法家、杨朱和墨子的学说。置身纷扰朝政,孟子何以独倡仁政?他与时代对话,捍卫人性与伦理。穿梭诸国,绝不妥协,只为理想社会下那份最纯粹的“正人心”。
02:05 孟子的政治努力与社会批判:民贼、禽兽与无政府主义
孟子生平的奋斗,有两个目标:一是在思想上发扬儒学; 一是从政治上推行仁政,也就是把儒家的理想实践出来。综观他的生平,显然政治方面的奋斗是劳而无功,但在更为基本的思想方面,却有惊人的成就。儒学的开创在于孔子,而发扬之功,则必须归给孟子了。
在孟子眼中,当时的思想学派,虽然错综复杂,但归纳起来,最主要的大致可分为四派:一派是法家、一派是杨朱、一派是墨子,还有一派就是他自己所属的儒家。因为孟子是以儒家的卫道者自居的,所以他大声疾呼要“正人心,息邪说”,要以儒家的力量去统一思想界。
他周游列国,提倡仁政,就是直接对法家的制裁。当时法家的偶像是管仲,孔子对管仲,有时批评,有时称赞。但孟子由于卫道,就不得不以管仲为攻击的目标。他认为那些替国君开辟疆土,充实府库,联合盟国,每战必胜的,这是现在所谓的良臣,在古代却是民贼。因为仁政是用的怀柔政策,而那些法家所用的是侵略方法。在以侵略为目标的军国主义下,人民的自由和生命是完全地被牺牲了,所以他们是民贼,是仁政的死敌。管仲就是第一号民贼;那些好功的法家、好战的兵家, 以及阴谋的纵横家,都是一大批的民贼。孟子所以在政治上处处碰壁,就是因为民贼猖狂;而他之所以急于从政,也无非是希望借政治力量以制裁民贼。
制裁民贼,这是孟子在政治上的努力。至于在社会方面, 他的目标却始终针对着杨朱、墨子。他曾激烈地说:“杨氏为我,是无君也。墨氏兼爱,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是禽兽也。” 孟子为什么这样冲动地骂他们为禽兽呢?因为以孟子的看法,杨朱只注意个人,忽视社群,是无政府主义;墨子不论亲疏, 忽略了伦理,是无家庭制度。两者都遗弃了社群生活和社会组织,而无从发挥人类社会的道德精神。这无异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,纵然活着,也不过是一种动物而已。所以孟子才骂他们为禽兽。不过这种如响斯应的流弊,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到的罢了。
-
孟子离开滕国时,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。到了梁国后, 惠王看到孟子,第一句话便问:“老先生啊!你从千里以外赶来,一定对我国有什么利益吧!”孟子一听这话,就看透惠王的用心是在于富国强兵,只知利害,而不问道义。孟子认为这是祸乱的症结,是他最痛心疾首的事。所以也就毫不客气的借题发挥,把惠王训了一顿,他说:“君王啊!你为什么一开口就是利呢?你可知道还有仁义吗?”接着向惠王解释:如果大家都以利字为前提,大家都只顾个人的私利,再也没有人肯为君主牺牲,肯为国家服务了。试问这样的话,国还何以成国?利还何以为利?但惠王当时一心只在于浅功近利,是不会了解这根本所在的仁义正道。因此孟子和他谈了好几次,都谈不拢。他喜欢玩乐,孟子却劝他与民同乐;他喜欢战争,孟子却劝他偃兵息战。他向孟子请教如何才能富国强兵,雄霸一代,孟子却把在齐国提的一套仁政的蓝图告诉他。惠王只觉得孟子迂阔,当然不会采用孟子的意见。后来惠王逝世,襄王登位。孟子一看他就不像个人君,毫无君主的风度,知道他不可能有作为,于是便只得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邹国。
此后,孟子曾一度到过鲁国,被小人臧仓所阻。这时孟子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,即使热情如昔,但衰弱的身体也不准许他再到处奔波了。所以他便结束了三十余年来的周游,回到邹国和学生们在一起谈论学问,把他的理想留了下来,成为《孟子》七篇。直到他八十四岁时,终于带着他满腹的热情,离开了人世。
-
虽然这时他已在政治舞台上辗转了十年,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然而他的壮志却一直燃烧着,所以在回到邹国不久,听说宋王偃有意要行仁政,于是便星夜赶向宋国。可是到了宋国后,兴奋的心情却凉了一半,因为这时宋王正被一群小人包围住,所以他感慨地对宋国一位忠臣戴不胜说:“如果宋王周围都是君子,他要做坏事也做不成。如果宋王周围都是小人,他即使要做好事,也不可能了。”
孟子似乎没有得到宋王的赏识,只是向宋大夫戴盈之提出仁政的措施。也许宋和齐的国情不同,这次的要求却比齐国的激烈。他主张税收应减低到什一,并且废除一切关税。戴盈之认为太激烈了一点,等待明年再实行。孟子便用比喻讽刺说:有一个人,每天偷邻居的鸡,别人警告他这是犯法的。他却回答说:那么让我慢慢地改过,每月偷一只,等到明年再洗手不干,试想这是否有点荒唐。孟子的意思,乃是借此说明要行仁政,就得立刻改弦更张,推延便是无诚意。
这时,孟子听说梁惠王正在招贤纳士,于是便准备回邹一行,再去梁国。
以前滕文公做世子时,曾因事经过宋国,和孟子谈得很投机。孟子认为滕国虽小,但截长补短,约有五十里,还可以行仁政。等到这次孟子返邹后,滕文公已经即位了,立志要行仁政,便派人去礼请孟子。孟子到滕后,也提出了他的一套仁政方案。他知道滕国土地偏少,应着重在分田制禄。他把土地分为“国中”(城里)和“野”(乡下)二种。在“野”的土地,每方里(九百亩)为一单位,每一单位划成九格,成井字形。旁边的八格分给八家农人耕种,叫作“私田”;当中的一格,八家共耕,由政府保留,当作税收,叫作“公田”。这公田的所得,就是给予贵族们的俸禄。至于“国中”的土地,不易划成“井”字,因此全部分给人民耕种,抽什一之赋。这是孟子的一套平均地权、减轻赋役的方法。然而他觉得滕国实在太小了,而且又夹在齐楚两国中间,朝不保夕;如果要完成商汤文武的事业,实在有点力不从心。因此他又想到了梁国。梁国就是战国七雄中的魏国,因为国都在大梁,所以又称梁国。
-
年轻的理想家孟子,拿着一份能换来民安富强的设计图纸,向王展示如何筑梦诸侯国。税减产增、灾消福至,岂不妙哉?然而面对拜金王,那一刻孟子深感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。心中理想国,何时能落实人间?善政养民的路,到底谁能引领?走吧,离齐国,依然怀抱一颗未泯的太平心志!
02:06 孟子的理想与现实: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挫折与失落
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民生问题,应该使人民上足以事父母,下足以养妻子。年岁好的时候,固然丰衣足食;年岁不好的时候,也足以糊口,不至于流离失所。而要达到这种程度,必须善为人民制产。如果能在五亩大的田宅中,种植桑树,五十岁的人,就都有布帛可穿了。鸡猪等家畜,不要错过它们交配繁育的时令,七十岁的老人,就都有肉类可吃了。每户百亩的田地,不要妨扰他们的耕种,八口之家,也都不至于挨饿了。其次应减轻佃农的税收和改良商品的关税,并且开放公家的园地,让人民自由田猎。除了增产减税外,同时更要安定社会,使做官的人有世代的俸禄,以及鳏寡孤独的人,都能安居乐业。能达到这种境地,才算是仁政。
齐宣王看了这个提议,不禁大声地赞美:“好极了,好极了。”孟子便紧接着问:“大王既然认为很好,为什么不立刻实行呢?”宣王却俏皮地回答说:“寡人有贪财好色的缺点啊!”尽管孟子极力劝宣王以民生为前提,但宣王却是别有居心,借辞推托。
虽然宣王对孟子非常恭敬,曾有意请他做公卿,并赐王禄万钟,以供养孟子师生。但孟子看透宣王已经怠于政事,把大权交给一位宠幸的大夫王驩 huan1 ,孟子连进见的机会也逐渐减少了,于是便决心离开齐国。
在回国的途中孟子颇为失意,一路上抑郁不欢。一位学生问他说:“以前老师曾教我们,不应该怨天尤人,现在你为什么心里很不痛快呢?”孟子便拉长嗓音回答说:“以前是以前,现在是现在。我听说每隔五百年,必有一位圣人出来。但由周代到现在已有七百多年,时间已过头了,照理应该有人才出现。老天不要天下太平,也就算了;如果要天下太平,试想,除了我,还有谁能挑这副担子呢?现在看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,又怎能不心烦呢?”这番话,正说出了孟子一生的抱负,正说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。
-
孟子名轲,生于周烈王四年(公元前 372 年)。他本是鲁国人,后来迁居邹地(今山东省邹城市),便成为邹国人。他的身世几乎与孔子相同,也是在三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,由母亲的抚育而成长的。但他没有孔子那般早熟,非但不学礼,而且调皮捣蛋,偏爱做些违礼的事情,孟母为他而伤透心思。据说他模仿性很强,每到一地,便模仿那些治丧屠狗之事,劝说不听,制止不住。使得孟母因他而迁居三次,这便成为历史上有名的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。
孟子这聪明的孩子,幸运的是既有贤母的培育,后来又遇到良师的教诲,才使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。他是被子思的门人所赏识,而加以培植的。子思是孔子的孙子,曾子的学生。因此孟子所学的是儒家的道术,而且是正统的儒学。
自孟子学成以后,便接过儒家的衣钵,教授生徒。他也和孔子一样,带着学生们,周游列国,去打开政治的门路;然后再通过政治以实现儒家的理想。
孟子比孔子迟熟,也比孔子晚了二十年才走上仕途。在他四十岁左右时,邹穆公才举他为士。然而当时邹国的政治非常混乱,孟子感觉到在自己的国家内,不能施展抱负,使政治走上轨道,这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,于是便离开了邹国。
离开邹国后,就是孟子周游列国的开始。他率领着一个庞大的布道阵营,后车有几十乘,学生有几百人,浩浩荡荡地向列国进军。
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齐国。
孟子的气派很大,他认为国君如果有心治国,就应该礼贤下士。因此他到齐国后,并没有先去朝见齐王,只是和平陆大夫孔距心、齐相储子等做朋友。后来齐王慕名,非常谦虚地向他请教,他才到齐都会见齐王。
孟子了解齐国地大人多,如果政治清明,一定可以成为泱泱大国。但他看出齐王的野心,却在于增广土地,消灭列强, 这是穷兵黩武的侵略行为,而不是他所主张的王道政策。所以他和齐王见面后,便提出了他理想中仁政的蓝图。
-
中国的思想,从春秋进入了战国时代后,正如一夜春风吹遍了江南堤岸,到处是青枝,到处是绿叶,到处是柳暗与花明。
在春秋时代,活跃的只有儒家。其他各派,虽然都已播种, 都在抽芽,但仍然是深埋在泥地里。到了战国初期,最先脱颖而出的是墨家。它与儒家对抗,左右相映,形成了当代的两大显学。接着另一派隐士的道家,也默默地在每个角落里寻找他们的天地。这种趋势,发展到战国中期,愈益激烈。这时,以前各派的思想愈变愈分歧,阵容也愈来愈复杂;儒家增入了许多假儒者,墨家分为三派,道家也混入了许多纵欲主义。再加上当时新产生的商鞅等法家,孙膑、吴起等兵家,苏秦、张仪等纵横家,以及许多清谈好辩的“稷下先生”。这时期思想的波动,已达到了高潮;而思想的怪诞和分歧,也是史无前例的。有的劝人像禽兽般恣情纵欲,如它嚣 xiao1、魏牟;有的劝人像石头般麻木不仁,如田骈 pian2 、慎到。这些荒谬大胆、光怪陆离的学说, 应有尽有。把整个战国时代,点缀得仿佛一个思想界的大观园。
这时,堂堂正正以仁政仁心为号召的儒家,反被冷落于一旁。在他们的眼中,儒家的学说,空疏迂阔,不合时务;而且所言过于平正,没有吸引力。可是在儒家的眼中,这些异说纷纭的各派各家,都只是标新立异、借奇鸣高而已;非但无补于世道,而且有害于人心,使得纲纪荡然,社会混乱。所以这时的儒家们,都深深地感觉到,要真正使国家走上治平之道,固然必须发扬儒家的学说;但要发扬儒家的学说,却首先必须
“正人心,息邪说”。
在当时的儒家中,最先有这个觉醒,有这层认识,而且一手挽转颓风,使儒家大放异彩的,即是我们的亚圣——孟子。
-
庄子这套“大而化之”的思想,并非只求自我解脱,并非只求顺天安命,而是别有一番经世的苦心。
他和孔、墨、老子等哲人,都处于一个混乱的衰世,他们所遭遇的问题相同,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相同,只是所努力的方向不同,所解答的方式不同罢了。孔、墨是直接从事于社会的改革,希望能大刀阔斧地解决问题;而他和老子却是在人类智慧的园地中辛勤地耕耘,希望智慧愈多,问题愈少,能不用刀剪,便把整个世界自然地美化起来。在这方面,老子给我们的是事物演化的自然原理,要我们能智慧地运用这些原理来处世;而庄子却教我们把这些原理活用到人生,使我们“由自然行”、与天地浑然而为一。唯其如此,才把道家的情调倾注到艺苑,而形成林泉高雅的艺术文学。
对于庄子,尤其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是: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形而上的新境界。虽然老子的思想曾触及这个境界,但老子所构建搭的都是些静的原则。至于庄子的境界,却是动的,是一片茂盛的生机。在这个境界中,他把形而下的世界做了一个返照,使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人间的悲剧,虽然是那么的亲切,但在超脱的心境上又是距离得那么远。在这个境界中,他塑造了许多理想的人物,和形而下的世界作了一个对比,虽然这理想是那么高不可及,但却是人类日日向往的世界。我们遍翻中外古今的哲学,对于形而上境界的描写,能有如此的生动,如此的亲切,如此的引人入胜,恐怕以庄子为第一人了。
然而不幸后人往往曲解庄子,认为他的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怀疑色彩,带有极度的虚无情调。殊不知这都是由于我们以世俗的观点来看庄子,反而把他这番至理,误为怪诞不经。其实庄子超脱的眼光看得非常真切,他要我们舍弃浅薄的是非观念;但他沉痛的批评,却显然说明了他本身有着激烈的是非感。他构搭了这个形而上的新境界,就是要扬弃人类的罪恶,把人性向上提携,向上推进。
今天,我们诵读他的“瑰玮”之文,那一字一句,都是智慧的鞭子,鞭在我们的灵魂上;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他那股热力,从字里行间,直透我们的内心,使我们兴起,使我们高扬,使我们超然物外,与他同游于纯真至美的境界。
-
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,不仅要知得真切,而且更要有心性修养上的实际功夫。因为嗜欲深者天机浅,一切的偏见执着都是由于欲念的作祟,所以我们要破除差别之相,首先应舍弃选择贪取之心;而要舍弃选择贪取之心,功夫就在一个“忘”字。
所谓“忘”,就是要忘毁誉、忘利害、忘生死、忘是非。因为这些都是欲念,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些欲念,就像鱼儿在陆地上以口沫相吸,只是苟延残喘而已。鱼儿必须“相忘于江湖”,才能优游自在;同样,人类必须是非两忘而化其道,才能逍遥自在,才能达到“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通”的境界。这时,不仅所有的苦患得失、舍弃一空,就是连自己的身心,也忘得一干二净,这种功夫,就叫作“坐忘”。
但坐忘并非形如槁 gao3 木,心如死灰,而是“相忘于道术”,而是有它活泼泼的生机。因为这时已证入了心通万物而无心的境界,这种境界,庄子曾有一段精彩的描写。
有一次,庄子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,在花丛中无忧无虑地飞舞,自以为得其所哉!得其所哉!不知道自己是庄周。可是等他醒了以后,却惊讶于自己是庄周。这时他有点莫名其妙:究竟是庄周做梦,梦见他变为蝴蝶呢?还是蝴蝶做梦,梦见它变为庄周呢?庄周和蝴蝶,本来是有差别的,现在他们融在一起,分不清孰是谁,谁是孰了。这种境界,就叫作物化。
物化后的庄子,已不是一飞冲天的大鹏,而是与天地融成一体,无所不在的精神了。这时,他不再逃避什么,也不再追求什么,在他的眼前,一切是平等的、和谐的。这时,他虽然超越世间,上与造物者游,但又回返人间,与世俗相处。他已是一团变化莫测的浮云,可以随心所欲地飘到哪儿就是哪儿,化作什么就算什么。人世的一切盈亏得失对于他还有什么意义呢?他正像一把火,薪木虽已燃尽,而精神的火焰却一直上升, 永远地,永远地!
-
然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,非但不了解这种妄见偏执,相反的,却争得非常起劲。我们都争大而舍小,羡贵而轻贱,求成而避毁,贪生而怕死,是己而非人。我们为了小名小利,便钩心斗角;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名小利,就沾沾自喜。这正像秋天涨水时的那些江河,看到百川支流,涌进了自己的怀抱,便得意忘形,以为天下之美,尽在于己。可是等到它流入了大海,看见白茫茫的一片,无穷无际时,才望洋兴叹,悔悟昔日的浅薄无知。人类行为的可笑可怜,也正是如此!
庄子这一连串的寓言,一连串的嘲笑,就是要我们舍小知而求大悟。他从天上放下了一根绳子,要把我们从这个褊 bian3 狭的世间中超度出来。这根绳子的作用,就是要我们打破差别之相。对于这点,他和惠施曾做过一次有趣的辩论。
有一次,他和惠施在濠 hao2 水的石梁上漫步,他心情很愉快, 便说:“你看水里的鱼儿们,从容地游着,多么的快乐啊!”惠施和他抬杠说:“你不是鱼,怎么知道鱼儿们的快乐?”他反问说:“这样说来,你不是我,又怎么知道我不懂得鱼儿们的快乐?”惠施很不服气地说:“我不是你,固然不知道你,但你也不是鱼,那么你也无法知道鱼儿们的快乐,这不是很明显的吗?”他却回答:“让我们回到起先的问题,你问我‘你怎么知道鱼儿们的快乐’,显然你已知道鱼儿的快乐,才问我怎么知道的,告诉你,我是在这石梁上体悟到的。”
在这段辩论中,可知惠施把彼此的界线分得很清,使物我相隔。但庄子能以自己的心去体现万物,由自己的悠然,以推知鱼儿们的快乐。因而拆除了樊篱,把彼此打成一片,把物我融为一体,以达到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,这境界,就是齐物思想的最高表现。
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,不仅要知得真切,而且更要有心性修养上的实际功夫。因为嗜欲深者天机浅,一切的偏见执着都是由于欲念的作祟,所以我们要破除差别之相,首先应舍弃选择贪取之心;而要舍弃选择贪取之心,功夫就在一个“忘”字。
-
探秘庄子的哲学世界!为何他能至高俯瞰纷扰人世?盘点我们追求欲望背后,是不是自寻的桎梏?什么是是非?又怎么判断?跟随大鹏的翅膀,一起飞越常人的樊笼,洞悉庄子的达观人生。
02:07 超越自我,突破偏见: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
04:08 纷纷争鸣的道德观点:庄子的困惑与感慨
庄子所以有如此的达观,如此的境界,乃是他有一套超然的思想,使他超然物外。
前面说过:他正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大鹏,在九万里的高空, 以尖锐的视力,观察着人间。但这只大鹏的前身,本是北海中的一只大鲲,这个北海象征了人间世;在这个狭窄的人间世里,充满了愚蠢无知,充满了烦恼和痛苦。所以他要化为大鹏,举翼高飞,冲开了人性的枷锁,冲出了世俗的樊笼,而奔向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天池。
当它直上九霄以后,再回顾这个碌碌的世间,看到那些芸芸众生都好像是地面上形形色色的窍穴。当大风起兮,万窍怒号,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;这些声音,虽然“吹万不同”,但都是一气的作用,都是由于每个窍穴的“自取”罢了。人间世的一切正是如此。
我们的欲念,正像一个个的窍穴,为了无尽的满足,而产生各种不同的追求。试看我们斤斤计较于大小、贵贱、成毁、生死、是非等等,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取的妄见呢?我们有比较心,才有大小的不同;有虚荣心,才有贵贱的差别;有得失心,才有成毁的感觉;有贪恋心,才有生死的烦恼;有偏执心,才有是非的争辩。事实上,从高一层的境界来看,却并无这些差别之相。就以是非的观念为例:
什么叫作“是”?什么叫作“非”?是非的标准又在哪儿? 庄子怀疑地说:“假定你和我辩论,你胜我输,试问果真你说的对,我说的就不对吗?反过来,你输我胜,难道我说的就对,你说的就不对吗?这里只有几个可能,不是你对就是我对,或者全对,或者全不对。我们两人囿 you 4 于成见,当然不能判断,那么请第三人来做裁判吧,可是究竟要请谁呢?与你意见相同的人,当然偏向你;与我意见相同的人,当然偏向我;与你我意见不同的人,他又有自己的意见;与你我意见相同的人,那就等于你和我,也无劳他来做裁判。所以我和你以及第三人都不能知道谁是谁非啊!”可见一般是非的观念,都只是个人的看法,都只是自取的偏见,所以才有儒墨之争,各张旗鼓,都以自己为是,以别人为非,都“是其所非,而非其所是”。使得庄子不禁感慨地说:“以我来看,仁义之端,是非之途,杂然纷乱,我又怎能知道其中的分别呢?”
-
他的内心虽然满怀着深忧,但他绝不像孔子一样叹道穷, 也不像墨子一样大声疾呼,他却相反地付之一笑。他从客观的立场来看主观的我,觉得一切都是可笑的,他的一切忧愁、快乐都是可笑。试看他的妻子死时,他的朋友惠施来吊丧,看见庄子正直着双脚,坐在地上,敲着瓦盆在唱歌。惠施奇怪地问:“她和你相伴一辈子,生下的儿子也已成人。她死了,你不哭一声,倒也罢了;反而敲盆唱歌,这未免太过分了!”庄子回答说:“不如你所说,她初死时,我哪里能无动于衷呢?但仔细一想,她本来是无生无形,毫无踪影的;突然有了这个形,又有了生命,现在她又死去,这不正像春夏秋冬,随时在变化吗?她也许正在一间巨室内睡得很甜呢?我却号啕地接连哭着,自己想想未免可笑,所以也不哭了。”这是一种把悲观和乐观消融在一起的达观主义。
庄子临死的时候,也是那么的达观。他的几个弟子商量, 如何好好地安葬老师。庄子便说:“我把天地当棺椁,日月当连璧,星辰当珠玑,万物当赍ji1品,一切葬具都齐全了,还有什么好商量的。”弟子们回答说:“没有棺椁,我们深怕乌鸦老鹰吃了你。”庄子微笑地说:“弃在露天,送给乌鸦老鹰吃;埋在地下,送给蝼蛄蚂蚁吃,还不是一样吗?何必厚此薄彼,夺掉这边的食粮,送给那一边呢?”
这是何等的达观,何等的境界!
-
穿破旧衣、挖苦诸侯,庄子的不羁又有谁能比?他游历世间,并非封官讨官,而是为了直书其言,揭示形形色色的虚伪。庄子一生时而隐居,时而周游,唯独在人生观念的探索上,无人能及。他斥儒衣之假,指出真知寥寥。玩世不恭却又深怀忧国的庄子,只有通过他的独到观察才能懂,听我道来庄周绝妙洞察。
02:04 庄子的嘲笑:揭示儒家的假象与真知灼见
04:07 庄子的独醒之道:嘲笑假道学与真君子
的确!庄子的一生,就是喜欢在泥地上拖着尾巴爬,是那么的潦倒,那么的玩世不恭。有一次梁王请他去聊聊天,他穿着一身大麻衣,已打满了补丁。脚上套着一双鞋,没有青丝鞋带,而是用麻带捆着,就这样不修边幅地去见梁惠王。惠王觉得他有点不像样,就问:“先生,你那样的潦倒吗?”庄子幽默中有刺地说:“人有了道德而不能实践,才是真正的潦倒呢!衣破了,履穿了,并不是潦倒;而且这是我遭遇时代的不幸,碰不上圣君贤相,又有什么办法呢?”这种当面挖苦君主,也只有庄子这样不羁的天才始能敢作敢为啊!
他的一生除了在漆园内过着与树木鸟兽为群的生活外,便是在外面东奔西跑。他的周游列国,可不是像孔子一样寻找一个政治舞台,也不像墨子一样热心于改革社会;而是到国外旅行一下,看看这人间世的可怜相,然后振笔直书,嘲笑尽这形形色色的一切。在表面上看来他极端的玩世不恭,好像是专以讥笑取乐似的;事实上他内心有着深忧,这种深忧与孔墨的忧国忧时并无不同。他有一次去见鲁君,鲁君问:“鲁国有很多的儒生,可是却很少有人向先生您学道。”庄子回答说:“鲁国的儒生也很少。”鲁君奇怪地问:“在鲁国到处可以看到穿儒服的人,怎么说儒生很少呢?”庄子说:“我曾听说,真正的儒生,戴着圆冠的,能识天时;穿着方鞋的,能知地形;挂着玉佩的,断事如神。有道的君子,并不一定要穿着儒服啊!衣服穿得漂亮的,未必真有学问哩!你一定不信我的话吧!那么你不妨下一道命令说:没有儒家的学问,而穿着儒服的人判他死罪。看看还有几人?”鲁君命令发下的第五天,鲁国只有一个人敢穿着儒服立在公门前面。鲁君就把他召进来,问以国事,果然随机应变,对答如流。庄子笑笑说:“偌大一个鲁国,真正的儒生只有一个人罢了,还能说多吗?”庄子的嘲笑,就是要嘲尽那些假道学,假君子。“天下皆醉我独醒”,他觉得“滔滔者,天下皆是也”!真正明眼的,只有他一人罢了。
-
有一次,宋国有一个曹商,奉宋王的命令出使秦国。去的时候,带车几乘;回来的时候,由于得到秦王的欢心,带回一百多乘车子。于是,便向庄子吹牛说:“叫我住在穷巷矮檐下,织着草鞋过活,我是没有这种刻苦的本领。而我的本领,只要一句话把万乘之主说开心了,便可拥有百辆的车乘。”庄子带着讥讽的口气说:“我听说秦王有一次生病,下诏求医。凡能替他开破脓疮的,赏一乘车;替他舐痔的,赏五乘车;做得愈卑鄙无耻的,得车愈多。你大概也替秦王医过痔吧!不然怎能得了那么多的车呢?好了,你快去吧!”这段讽刺是多么的泼辣、尖刻,更可看出庄子对于那些以“无耻”所换来的荣誉、富贵的深恶痛绝!
他非但对于金钱不十分重视,对于功名也看得很开。有一次他到梁国去看惠施,有人向惠施挑拨说:“庄周的口才比你好,他来了,你的相位便难保了。”惠施着了慌,便通令在城中搜寻他三天三夜。结果他登门去见惠施,说:“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名叫鹓鶵 的鸟吗?它从南海飞向北海,在辽阔的途程中,不见梧桐不宿,不遇竹实不吃,不逢醴泉不饮。正在它飞时,下面有一只鸱chī,口里正衔着一只腐鼠,那只鸱生怕鹓鶵 来抢它口中之物,急得仰头大叫一声:‘吓!’现在你也想把梁国的相位来向我吓一声吗?”
事实上,庄子非但不会去争取别人的相位,即使把相位恭恭敬敬地送给他,他也不会接受的。有一次楚王喜欢他的才气,派了两位大夫去礼聘他。那时他正在濮pu2水边钓鱼,两位大夫恭敬地说:“我们国王,有意把国事麻烦你先生。”庄子不动声色,爱睬不睬地说:“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,死了已三千年,你们楚王把它用锦巾包着,绣笥si4盛着,藏在太庙里,以卜吉凶。试问这只神龟真正有灵的话,宁愿死了留着一套龟甲受人尊重呢?还是宁愿活着,在泥路中拖着尾巴爬呢?”两位大夫说:“以神龟来论,当然宁愿活着,在泥路中拖着尾巴多爬一会呢!”
- Показать больше